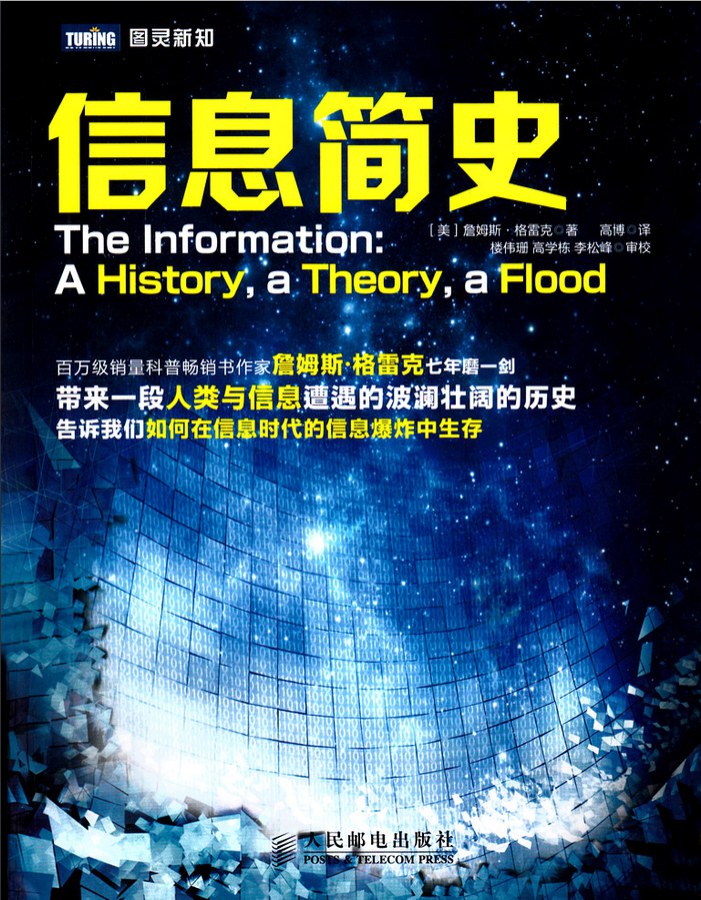312.「用复杂性的这种定义来衡量的话,一百万个零与抛掷硬币一百万次分处于两个极端。空字符串是简单的极致,而随机字符串则含有最大的复杂度。零没有传递任何信息,而抛掷硬币则生成了最大的信息量。不过,这两种极端情况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很无趣,并且毫无价值。如果它们当中一个是来自其他星系的讯息,那么我们可能不会认为发送方是智慧生物。而如果它们表示的是音乐,它们同样也没有价值可言。我们关注的东西大都是居于两个极端之间,处于模式与随机彼此交织的地带。」
书籍名称:《信息简史》
基础信息:[美] 詹姆斯·格雷克 / 2013 / 人民邮电出版社
豆瓣评分:8.6/10
豆瓣链接: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5752043/
读完时间:2021-06-24 17:28:45
我的评分:4.0/5.0
我的标签:#2021,微信读书
免责声明:本页面所发布的笔记仅用于分享我在阅读过程中的摘录、总结和反思。内容大多为书中原文或书中观点的简要提炼,并不代表我个人的立场、意见或价值观。书中观点仅供参考,如需深入了解或采纳,请参考书籍的原始内容。
阅读笔记:
《信息简史》詹姆斯·格雷克 (2021/6/22 10:16:16)
信息简史
詹姆斯·格雷克
63个笔记
引子
在22岁那年,香农在硕士论文中把一个19世纪的思想,即乔治·布尔的逻辑代数,应用到了电子电路的设计上。(逻辑和电,这是多么不寻常的组合!)后来,他又有机会与数学家、逻辑学家赫尔曼·外尔合作,后者教给他什么是理论:“理论允许意识‘跳出自身的影子’,超越经验而把握超验,但这只能借助抽象符号实现(这一点是不证自明的)。”
现在很难还原在香农之前的人们所面对的世界图景。尽管我们可以阅读他们留下的著作,但我们很难重拾那种无邪、无知而蒙昧不察的状态。
第1章 会说话的鼓(似是而非的编码)
可用的符号越少,为表示出给定信息量所需传递的符号数就得越多。对于非洲的鼓手来说,需要传递的符号数是对应口语的八倍之多。
第2章 持久的文字(心智中并无词典)
借助文字,一个人可以向众多人说话,死者可以向生者说话,生者可以向未生者说话。正如麦克卢汉所言:“柏拉图作出这番观察时,他无法知道西方世界接下来的两千年都将是手抄本文化。”[插图]这种首次出现的人工记忆,力量之大无可估算:它重构了人类思维,人类历史由此发端。直到如今,它的力量仍然无法估算,但从一项数据可以略见一斑:任何一种口语的词汇仅包含数千个单词,而被最广泛使用的书面语言——英语,有记录的词汇就超过百万之众,而且其数量还在以每年数千个的速度持续增长。此外,这些字词并不是只存在于当下,每个字词都有其渊源和演变至今日模样的历史。
蚂蚁会喷洒信息素,留下化学信息的痕迹;忒修斯会散开阿里阿德涅的线团以防止在迷宫中找不到返回的路。
说话声音的停留是如此短暂,所以偶然出现的回声现象,即一个声音被听见两次,甚至会被当成一种魔力。老普林尼曾写道:“对于这种神奇的声音回响现象,希腊人赋予它一个漂亮名字,称其为厄科女神(Echo)。”[插图]
由于汉字的基本单元是字,因而所需符号的数量成千上万。这一方面颇有效率,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诸多问题。汉字统一了使用各种各样口语的人群,口语不通的人们之间可以通过文字交流。汉字含有至少五万个符号,其中有六千个左右为大多数识字者所常用和掌握。他们通过流畅、示形的笔画,在汉字中纳入多层维度的语意关系。一种方法是简单的重复,比如三木成森;更抽象一点的,如日月为明,以及二[插图]为[插图],即一周天。而复合造字过程就更令人惊讶了,比如以刀收禾为利,以手翳目为看。汉字还可以由构成元素的相对位置不同而区分含义,比如直立为[插图](人),横陈为[插图](尸)。有些构成元素用以表声,有些甚至有双关的含义。汉字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演化出来的最丰富,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文字系统。从所需符号的数量之多以及单个符号传递的意义之广来看,汉字是一种极端个案:符号集最庞大,单个符号的含义也最丰富。文字系统也可以采取不同的途径:符号数量较少,而每个符号的含义也较少。这样一种中间形态的文字就是音节文字,即基于音素的文字系统,使用单个字符表示音节,这些音节可能带有意义,也可能没有意义。数百个这样的字符,也可以构成一门语言。
位于另一极端的文字系统出现得最晚,这就是字母文字,使用一个符号代表一种最基础的声音。字母文字是所有的文字系统中最简化的、最具颠覆性的东西。地球上的所有语言中,“字母表”这个词都是同一个:alphabet(alfabet、alfabeto、aлфaвит、αλφάβητo)。字母表在历史上仅被发明过一次。所有已知的字母表,无论是到今天还在使用的,还是写在考古发掘出来的泥板和石块上的,都只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它起源于靠近地中海东岸的地区,时间上略早于公元前1500年。
古文字学家面临着一个该专业独有的起源问题:只有在文字发明以后,探究文字本身的历史才有可能。对此,20世纪字母研究的权威之一戴维·迪令格尔,曾引述前人的说法:“没有人能够坐下来然后宣布:‘现在,我即将成为能够书写的第一人。’”
“通常,它们无言地诉说着不在场者的话语。”
还有很多契据是以“再见”结尾的。在书写文字成为自然而然、成为人类的第二天性之前,这些来自口语的遗响必须先逐渐清除。文字本身必须重塑人类的意识。
第3章 两本词典(我们文字的不确定性以及我们拼写的随意性)
语言并不像一个单词仓库,用户无法从中随时“调出”现成的正确单词。相反地,口语词稍纵即逝,消失无踪。当单词被说出来时,人们无法将其在各种形式之间加以比较和衡量。而当人们将羽毛笔蘸饱墨水、准备在纸上写下一个单词时,他们每次都可以进行新的选择,选定一些自觉合适的字母组合来达成目的,只是这样的选择不一定每次都相同。随着印刷书的出现和普及,人们逐渐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即单词的书写形式理应是确定的。也就是说,只有一种拼法正确,其他的都是错误的。起初,这种感觉是潜意识的,但后来就进入了众人的意识当中。出版商于是自告奋勇担当起规范化的责任来。
第4章 将思想的力量注入齿轮机械(喔,欣喜若狂的算术家啊!)
任何多项式函数都可以通过差分法来降阶,并且所有良态(well-behaved)函数,包括对数函数,都可以以这种方法来有效逼近。更高次数的方程需要用到更高阶的差分。
当他在铁轨上行驶时,他意识到蒸汽机车有一种特有的危险:由于它的运行速度已经超出了先前所有通信手段的速度,因而火车之间无法及时了解相互的位置。除非所有的火车都能遵循最正规、最严格的调度,否则险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其他人也同样担心火车运行与通信沟通之间的速度差。一位很有影响的伦敦银行家告诉巴贝奇,他不喜欢这种新的交通方式:“这让我们的职员有可能监守自盗,然后以每小时三十多公里的速度逃往利物浦,再从那逃往美国。”
至于那台分析机,它在重新被人记起之前,先得被人遗忘。它没有留下明显的子嗣,因而当它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时,它就像是被重新发现的宝藏,引起了人们的阵阵惊叹以及种种困惑。在现在这个计算机如日中天的时代,历史学家珍妮·厄格洛从巴贝奇的机器中感受到了“另一种时代错位感”。[插图]她写道,这样的失败发明包含着的“思想,就像是静躺在黑暗橱柜里、慢慢泛黄的蓝图,等待着被后世再次偶然发现”。巴贝奇的机器的初衷是生成数表,但到头来,其现代形式反而导致数表被废弃。巴贝奇可曾预计到这一点呢?不过,他的确曾好奇未来的人们将会如何利用他的远见。按他的猜测,至少还要再过半个世纪,才会有人再次尝试构造一台通用计算机器。而事实上,过了将近一个世纪,这项工作所必要的技术基础才准备就绪。巴贝奇在1864年写道:“如果有人在未被告诫以我的前车之鉴的情况下试图尝试这项如此了无指望的工作,并通过完全不同的原理或更简化的机械手段而成功实现了一台可与整个数学分析部门相当的机器,那么我不怕把自己的名誉托付给他,因为他肯定会完全理解我当年努力的性质及其成果的价值。”[插图]
第5章 地球的神经系统(就那么几根破电线,我们能指望它什么呢?)
诺莱组织了一次实验,利用一个莱顿瓶和一根铁丝,向围成周长一英里的一个大圆的两百个卡尔特教僧侣发送一次电击。从这些僧侣们几乎同时的惊跳蹦叫中,观察者很容易判断出,一个信息量不大却也不为零的讯息是以多么惊人的速度通过了此圆圈。
即使讯息成功抵达,也仍然不能完全采信。中继信号塔很多,这就意味着出错的几率很大。世界各地玩过传话游戏的孩子都知道这个道理,在英国这个游戏叫做中国悄悄话(Chinese Whispers),在中国叫做以讹传讹,在土耳其叫做咬耳朵(From Ear to Ear),而在现代美国则直接叫做打电话(Telephone)。
通过键式电报,操作员可以把发送信号的工作速度提高到每分钟数百个,毕竟这些信号只不过是电流的中断而已。
我们不用费多大劲就能意识到,这个事实是现在正在发生的,而不是已经完成的。
还有位男士带着一份“讯息”来到缅因州班戈区的电报局。操作员在电报键上操作完毕后,就把写有讯息的纸条摁到了钩子上。不料,这位客户投诉说,讯息根本没有被发送出去,因为他明明看到它还挂在钩子上。
在多种意义上,使用电报就意味着用编码(code)书写。摩尔斯的点划系统一开始并未被称作一种编码,而仅仅被称为一种字母表:“摩尔斯电报字母表”就是当时人们对它的普遍称谓。但它并不是字母表,因为它并非以符号表示声音。摩尔斯的方案是以字母表作为起点,通过替代(用新的符号替换旧的符号)来对其加以利用。它是一种元字母表,与字母表已经隔了一层。这种将意义从一种抽象转换为另一种抽象的过程,在数学中早已有之。并且从某一方面上说,这恰是数学的本质所在。而现在,它已经成为了人们熟悉的一种思维工具。正是由于电报的功劳,到了19世纪末,人们逐渐适应或至少熟悉了编码的概念:用以表示其他符号的符号,用以表示其他词语的词语。从一种抽象向另一种抽象的转换,这就是编码(encoding)。
到了19、20世纪之交时,伯特兰·罗素给予了乔治·布尔非同寻常的赞颂:“纯数学是由布尔在其《思维的规律》中发现的。”[插图]这句话经常被人引用。不过,真正使其赞颂非同寻常的却是紧跟其后但很少被人引用的批评:他也错误地以为自己是在讨论思维的规律。但事实上,人们实际是如何进行思考的问题与他的研究并不相干,况且要是他的著作真的包含思维的规律,那么奇怪为什么此前没有一个人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思考呢?这不由让人感到,罗素对悖论还真是乐此不疲。
第6章 新电线,新逻辑(没有别的什么东西比它更严密地为未知所包裹)
铁丝网得到了广泛应用,用来界定私人领地以及在公共牧场中圈地。在高峰期,美国的农场主、牧场主以及铁路公司一年的铁丝网铺设量超过了一百万英里之多。从整体上看,全国的铁丝网构不成一个网络,只不过是彼此断开的一个个点阵,毕竟它们的本意是隔离而非连接。除此之外,即便在干燥的天气下,这些铁丝也是糟糕的导电体。但铁丝毕竟是铁丝,克劳德·香农并非第一个发现这种广泛分布的点阵有潜力作为通信网格的人,生活在偏远地区的数以千计的农场主也想到了这一点。他们不愿坐等电话公司从城市出来,于是决定自己组建铁丝网通信合作社。他们把固定铁丝的金属U形钉换成了绝缘的夹子,往铁丝网中添加了干电池和通话筒,并用额外的铁丝把断处连接起来。1895年夏,《纽约时报》曾报道:“毫无疑问,大量简陋但有效的电话设施正在源源不断地兴建起来。比方说,南达科他州的一些农场主自己架设了一套有八英里长线路的电话系统。他们自己安装了电话送话器,并借助当地用作护栏的刺铁丝网彼此连接。”
其中一个悖论是贝里悖论,它由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馆员G. G.贝里(G.G. Berry)首次向罗素提出。这个悖论与描述某个整数所需的音节数目有关。一般而言,显然数越大,用来表示它的音节数目也越多。在英语中,需要两个音节描述的最小整数是7(seven),需要三个音节描述的最小整数是11(eleven)。121乍看上去需要六个音节(one hundred twenty-one)来描述,但略施巧技,实际上四个音节就够用:“11平方”(eleven squared)。然而,即便绞尽脑汁,由有限个音节构成的名字必定是有限的,因而按罗素的说法,“必有一些整数的名字由至少十九个音节构成,而这些整数中必有一最小数。因此,不可能以少于十九个音节命名的最小整数必定指的是一个确定的整数[插图]”。[插图]但这里就出现了悖论。不可能以少于十九个音节命名的最小整数(the least integer not nameable in fewer than nineteen syllables)这个短语只含有十八个音节。这样,不可能以少于十九个音节命名的最小整数却以少于十九个音节命名了。
高举逻辑学和实在主义的旗帜抵制形而上学。
《数学原理》这部巨著体现的是一个曾短暂占据主流、无所不包的形式体系,哥德尔甚至采用书名的缩写(PM)来指代这个体系。当他提及PM时,他指的是那个体系,而非那部书。在PM中,数学就像是一只被包含在瓶子里的模型船,再也不用担心会被无常的大海推来搡去。
电报花了数年才做到的事,电话在数月内就做到了。当初它还只是个科学玩具,有着无穷多种可能的实际应用。而下一年,它就成了一个有史以来最为复杂、最为便捷、扩张得也最为迅猛的通信系统的基础……不久以后,商务办公室之间通过电话相连将成为常规而非例外。
信号作为一种抽象实体,与作为其载体的电流并不是一回事。
数学家还倾向于把他们面对的任何情况都加以理想化。他的气体是“理想气体”,他的导体是“全导体”,他的表面是“光滑表面”。他会把这称为“直抵本质”,工程师则恐怕会说这是“无视事实”。
第7章 信息论(我想要的不过只是一颗寻常的大脑)
建立一套有关信息及其处理的理论,有点儿像建造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你可以从东海岸出发,先试着理解信息是如何处理的,然后向西迈进。或者你也可以从西海岸出发,先试着理解信息到底是什么,然后向东深入。我们希望的是,两条铁轨能在中间会合。——乔恩·巴怀斯(1986)
(如果允许无限个符号,那么符号之间的差异将会任意小)
在香农看来,模式就等同于冗余。在日常语言中,冗余可以辅助理解。可在密码分析中,冗余就是密码的阿喀琉斯之踵。那么冗余又在哪里呢?在英语中,一个简单的例子是,紧跟在字母q后面的字母u就是冗余,即便把它去掉也不会有影响。[或者说,几乎总是冗余。要不是英语中还有极少的外来词,如Qin(秦)或Qatar(卡塔尔),它就完全成了冗余。]在字母q之后,大家都预期后面会是字母u。这里面不存在什么意外,它也就没有贡献什么信息。紧跟在字母t后面的字母h也有一定的冗余度,因为它是最可能在此出现的字母。香农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有一定的统计结构,以及相应一定的冗余度。我们可以用D来表示冗余度(这是香农的提法)。“在某种意义上,D度量了某种语言的文本在不损失任何信息的前提下能够缩减多少篇幅。”[插图]
在一条包含“母牛”一词的讯息中,即便后面间隔了许多其他字符,再次出现“母牛”一词的概率仍然相对较高。在香农看来,一条讯息就像一个动力系统,它的未来走向会受到过去历史的影响。
第8章 信息转向(形成心智的基本要素)
香农和维纳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维纳用熵来度量无序程度,而香农用熵度量的则是不确定性。不过,正如他们所意识到的,两者从根本上说是一回事。一个书面英语样本中的内在有序性越强(有序性表现为为语言使用者有意识或下意识所知悉的统计特征),其可预测性也就越高,换用香农的话来说,也就是后续字母所传递的信息量越少。如果受试者对下一个字母是什么信心十足,那么这个字母就是冗余的,它的出现没有贡献新的信息。信息是出人意料。
图灵在当年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其中一开头便令人兴奋:“我想请大家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机器能思考吗?’”[插图]而对于机器和思考这两个含义模糊的词,他认为即便对此不加定义,也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他的做法是,用一个测试来代替这个问题,他称之为“模仿博弈”,也就是后来鼎鼎有名的“图灵测试”。
当时的人们似乎认为,数字计算机的魔力本质上来源于电,并且神经系统的本质也是电。然而,图灵所努力要做的是,从最一般的抽象角度来思考计算的本质。他知道,这与电毫不相干:由于巴贝奇的机器没有用到电,并且所有的数字计算机在某种意义上又都是等价的,我们可以得出,电的这种使用并没有什么理论上的重要性……因此,数字计算机和神经系统都使用电这一特征,其实只是非常肤浅的相似性而已。[插图]
巴甫洛夫对于“心理学”一词及其所有相关术语都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根本不存在什么心智,有的只是行为。所谓心理状态、思想、情绪、目标、目的等,全是无形的、主观的、不可把握的东西,不可避免地会沾染到宗教和迷信。詹姆斯视为心理学核心课题的东西,比如“思想流”、“自我意识”、对时空的感知、想象力、推理能力以及意志等,在巴甫洛夫的实验室里都不见踪影。科学家能观察到的只有行为,并且行为至少能够被记录和测量。行为主义者,以美国的约翰·华生和后来非常知名的B. F.斯金纳为代表,基于刺激(如铃铛、食丸、电击)和反应(如唾液分泌、按操作杆、走出迷宫)建立了整个的科学体系。华生认为,心理学的全部目的在于预测某个特定的刺激会引发怎样的反应,以及某个特定的行为要源自怎样的刺激。在刺激与反应之间是一个黑箱,人们只知道它由感官、神经通道和运动机能组成,却无法通过科学方法对其进行分析。事实上,行为主义者无非是又说了一遍“灵魂是不可言喻的”。由于在条件反射和控制行为方面取得的成果,行为主义兴盛了约半个世纪的时间。
用心理学家乔治·米勒的话讲,行为主义者大概会说:“你们说什么记忆,说什么期待,说什么感觉,说了那么多心智方面的东西。这些都是虚的,否则秀一个给我看,指一个给我瞧。”[插图]而他们则甚至能教鸽子打乒乓球或是教老鼠走迷宫。然而到了20世纪中叶,不满的情绪开始显露出来。行为主义只研究可观察对象的前提变成了教条,它对心理状态的一概排斥成了束缚自身发展的牢笼,而心理学家依然渴望理解心智到底是什么。
第9章 熵及其妖(你无法通过搅拌将果酱和布丁区分开来)
因此,熵不是能量的一种,也不是能量的数量,而是如克劳修斯所说,是能量的不可用程度。
密闭容器内的气体从混合变得区分开来,这在物理定律上并非不可能,只是概率极其小罢了。因此,热力学第二定律只是在概率意义上成立:在统计上,万事万物都将趋于熵最大化。
这个妖则是用具有目的性的行为替代了这种随机性。它用信息降低了熵。
然而,信息是物理的(information is physical)。麦克斯韦妖则在两者之间架起了桥梁,它每处理一个粒子,就是做了一次信息与能量的转换。齐拉特发现(当时他并未使用信息一词),只要精确核算每次度量和记忆,这种转换也是可以精确计算的。根据他的计算,每获取一单位的信息总是会相应带来一定的熵增加——具体来说,熵会增加k log 2个单位。这个妖每次在两个粒子之间作出选择时,都会消耗一比特信息。
在统计力学中,熵度量的是一个物理系统的微观状态的不确定程度,即处于所有可能微观状态中的一种的概率。这些可能微观状态的出现概率不一定相等,因此,物理学家的公式是:S=-Σpi log pi。而在信息论中,熵度量的是一条讯息的不确定程度,即身为由信源发出的所有可能讯息中的一条的概率。这些可能讯息的出现概率不一定相等,因此,香农的公式是:H=-Σpi log pi。
生物使得通常的熵计算变得更复杂了。类似地,信息也会如此。布里卢安就问道:“取一份《纽约时报》、一本讲控制论的书,以及一堆分量相当的废纸,它们的熵一样吗?”如果你拿它们来烧火炉,自然它们的熵是一样的。但如果你是拿它们来读,那它们的熵就不同了。
有些人认为,齐拉特的论文为麦克斯韦妖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根钉子。但这并不是麦克斯韦妖的结束——还远远没有。要想彻底解决该问题,驱走这个妖,要求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一个与热力学相隔甚远的领域:机械计算。
第11章 跃入模因池(它其实就是寄生在了我的大脑里)
理查德·道金斯就在基因进化与思想进化之间建立起了他的联系。在他看来,主角是复制子,至于复制子是否由核酸组成则无关紧要。自然选择的规律是,“所有生命通过可自我复制的实体的生存差别[有的复制子存活,有的死亡]实现进化”。哪里有生命,哪里就一定有复制子。或许在其他世界里,复制子也能从硅基化学物质中产生——又或者完全与化学物质无关。
丹尼尔·丹尼特曾有一番妙论:“一辆四轮马车不仅是在各个地方之间运送了谷物或货物,也是在各个心智之间传递着四轮马车的卓越思想。”
第12章 认识随机性(僭越之罪)
那什么又是没意思的数呢?这大概就是随机数了。1917年,英国数论学家G. H.哈代随便搭了一辆编号为1729的出租车去探望生病的数学家斯里尼瓦瑟·拉马努金。他向拉马努金提及,1729这个数“相当无趣”。但拉马努金回应说,恰恰相反,1729是能用两种方式写成两个立方数之和的最小数。注10诚如数学家J. E.利特尔伍德所说:“每个正整数都是拉马努金的朋友。”由于这则轶闻,1729现在常被称为哈代-拉马努金数。
然而,拉马努金的心智毕竟是有限的,维基百科乃至人类的所有知识也是有限的。因此,有意思的数的列表终究会在某处终结,一定存在某个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的数。但无论那个数是多少,它都摆脱不了一个悖论,因为它总是可以被称为“最小的没意思的数”。
这正是另一种形式的贝里悖论,也就是罗素在《数学原理》中曾提到的那个悖论。他们问了个刁钻的问题:什么是不可能以少于十九个音节命名的最小整数?但不管它是多少,它都能用十八个音节来表达:不可能以少于十九个音节命名的最小整数。
有些涉及数学事实,比如一个数是否能用两种方式写成两个立方数之和。还有些则与世界、语言或人类的事实相关,并且这种关系可能是偶然的、短暂的,比如一个数是否对应着某个地铁站号或历史日期。
女钢琴家万达·兰多夫丝卡(Wanda Landowska)就形容它是“用断断续续的和弦实现了极致的和声”。
至少某些音乐可被认为是信息贫乏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作曲家约翰·凯奇(John Cage)那支题为《四分三十三秒》的作品,其中根本不包含任何“音符”。作曲家端坐在钢琴前,一动不动,持续四分三十三秒,作响的只是周围的声音——听众在座位上的挪动身体声、衣服的沙沙声、呼吸声和叹气声等。
用复杂性的这种定义来衡量的话,一百万个零与抛掷硬币一百万次分处于两个极端。空字符串是简单的极致,而随机字符串则含有最大的复杂度。零没有传递任何信息,而抛掷硬币则生成了最大的信息量。不过,这两种极端情况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很无趣,并且毫无价值。如果它们当中一个是来自其他星系的讯息,那么我们可能不会认为发送方是智慧生物。而如果它们表示的是音乐,它们同样也没有价值可言。我们关注的东西大都是居于两个极端之间,处于模式与随机彼此交织的地带。
第13章 信息是物理的(万物源自比特)
霍金第一个明确指出,或可以说警告道,这个问题威胁到了量子力学的根基。如果信息会消失,这就违反了幺正性,即所有可能事件的出现概率之和总是为一的原则。
第14章 洪流过后(一本宏大的巴别相册)
这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941年出版的短篇小说《巴别图书馆》的开场白。小说描写了一座神秘的图书馆,其中收藏了所有语言的所有书,包括验证和预言了每个人行为的书,福音书、福音书的注解以及福音书的注解的注解,详细到分钟的未来历史,所有书的所有改写版本,以及图书馆的正确书目和不计其数的错误书目,等等。这座图书馆(有人称之为宇宙)珍藏了所有信息。但你在其中却找不到知识,这恰是因为所有知识都在里面,与所有谬误混淆难分。无数的书架摆放在同样无数一模一样的六边形平台上,在那当中你能找到所有可能的一切,却也找不到想找的一切。这无疑是信息过载最完美的例子。
“通过清点我们所幸还拥有的。七部埃斯库罗斯的剧作,七部索福克勒斯的,以及十九部欧里庇得斯的。”塞普蒂默斯回答道。至于其他的,你不该比诸如遗失了你第一双鞋上的鞋扣,或长大后丢失了你上学时的课本之类更悲痛。如同将所有东西都抱在怀里的旅行者,我们有捡起,必然也有丢落,而我们丢落的自有后来者捡起。前路漫漫,人生苦短。我们在旅途中难免一死,但除去旅途本身,我们没有什么好失去的。索福克勒斯散佚的剧作将会一片一片地重新面世,或被用另一种语言写出来。无论如何,根据博尔赫斯的说法,所有散佚的剧作都能在巴别图书馆中找到。
维基百科以继承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事业为己任,试图收集所有已知的知识。但它并不是收集或保存现有的文本,而是尝试总结公认的知识(这不同于个人观点或原创研究)。
“维基不是纸”,这可算是维基百科非官方的座右铭。不无自指地,它也有了自己的条目(并且除英语版外,还有德语版和法语版)。它意味着,条目的数量或长度并没有物理的或经济的限制。比特是免费的。正如威尔士所说:“任何围绕纸张或空间的隐喻都已死。”
全世界所有的摇滚乐队也形成了一个名字空间,在其中“‘漂亮男孩’弗洛伊德”、“平克·弗洛伊德”和“粉红佳人”(P! nk)可以并行不悖,“第十三层电梯”、“第九十九层电梯”以及Hamadryad也是如此。只是想要在这个空间里想出新名字,难度已经变得越来越大。
第15章 每天都有新消息(或者诸如此类)
人们会收到太多讯息,却没时间去读。这也意味着,真正重要的讯息会淹没在一大堆不太重要的讯息中而难以识别。未来,当讯息系统变得越来越庞大、系统之间的互联越来越紧密时,这将会成为一个影响到此类系统的几乎所有用户的问题。[插图]
尾声(意义的回归)
正如博尔赫斯在《巴别图书馆》里所写:“我知道有一个陌生地区,那里的图书馆员对于试图从书中寻找意义的徒劳而迷信的习惯嗤之以鼻,以为这就好比试图从梦境或混乱的掌纹中寻找意义。”
微信读书